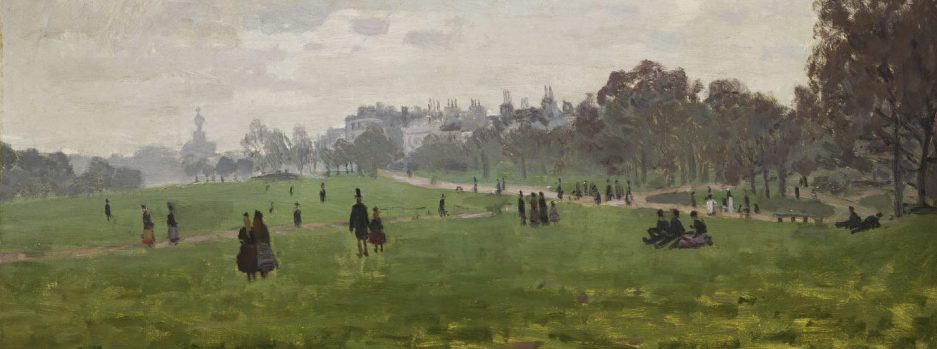云山几盘,江流几弯——章伯钧在一九五七
详细记述了一九五六到五八年间“整风”运动的始末,民主党派人士从被鼓励“鸣放”到被划为右派和打倒,父亲最早妥协,但事件的影响比一两人的仕途和宪政理想要深远得多,那些参与了批斗的民主人士,同样在运动后期被主动“交心”,自此民主党派成了“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”,元老沈钧儒还在衣袋里放着一张“你是不是听党的话”的字条来时刻警戒自己。还在读中学的我坚决跟父亲站在一起,政治课上要求写思想汇报,我不假思索地写道:“我不大相信共产主义,因为从来没人见过!”
谙熟人情世态的人都知道:事情超过了限度,就要翻过来,一定要翻过来!更何况他是毛泽东。
每一种妥协,都是放弃。
成熟的人可以为高尚的目标,卑贱地活着。
貌似一样怜才曲,句句都是断肠声——《李宗恩先生编年》读后
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李宗恩,在“反右”运动因与章伯钧牵连(其实就是几次座谈)而下放云南,直至最后去世仍未能摘掉帽子,本文记述了他高风亮节的一生。从抗战时领导贵阳医学院,到一九四九年选择留下(因为“协和”在北京,不在台湾,就这么简单),从五二年“三五反运动”时响应号召“自我反省”,到五七年被“划右”(右派言论包括对医学院学制的建议,反对中医介入,对“协和”工作的评估等),忍辱负重举家迁往云南。被改造期间,李宗恩坚持给农工民主党组织部写信,并上交党费,让人瞠目的是从未向共产党低头,其中缘由早已沉入历史的海底了,不管是因为不懂政治的天真,还是受西方教育而形成的独立意志,亦或是基本的人情人性,都令人万分敬佩。
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,丧失了人的尊严,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,不管人家怎么用,怎么揉,怎么踩,都无所谓的时候,才能脱胎换骨,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。(见朱锡侯先生自述《昨夜星辰昨夜风》)
左派反感你,同类“右派”也嫌弃你。都说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,其实没有半点人性,半点人情。
屠狗功名,雕龙文卷,岂是平生意?——怀想储安平
对报人和作家储安平的简略怀想,重点提到上任《光明日报》伊始对办报大刀阔斧的改革,和作者对《英国采风录》的喜爱,性情中人如储安平时常浮现在年老的我的思绪中,“他们像瑰丽却肃杀的秋景,搅碎了人生如梦的愁肠”。
他是不倦的风,始终呼啸着——说邵燕祥
诗人邵燕祥是一九八零年右派身份获得改正的那批“归来者”之一,是“不幸中的幸者”,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,而且并没有狭隘地把自己“看成是历史牺牲品”,而是“共谋者”,二零零七《新年试笔》中的“自我救赎”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觉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。邵燕祥的文字饱含锋芒,生活中诡谲幽默,待人宽宏,慈悲心肠(从对待诗人和干部袁水拍的态度就能清楚看得出来),“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”。
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——五十年无祭而祭
不同意徐贲先生所说纪念反右“不是要算账还债”,因为我们在对抗遗忘和“厘清历史是非对错”上做得远远不够,“共同记忆”和“灾难见证”早已失去,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写出来,不仅是上层的“贵族”,还有底层的“饥饿”。又谈到汉娜·阿伦特所述极权主义的恶,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悲剧的根源(举了丁玲、陈企霞的例子),“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人,才使一部国家机器、一个政党意志,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”。“五七史”是人祸史,背叛史,独裁史,道歉是“起码的事”,向加害者索赔更“是应该的”。
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,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,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?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和可怜的孩子。
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、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,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。
一半烟遮,一半云埋——周绍昌《行行重行行》序
对五五届北大中文系学生的杂忆,那一届人才辈出(大多数家境富裕,出身良好),“老师有个性,学生也有特点”,被打倒的右派也不少。五十年来,他们中的大多数“小心翼翼,碌碌无为,还有畏缩恐惧”,“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”苦难,“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、保健、子女和退休金”。周绍昌是个例外,他拿起了笔把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写了下来。
在我们这块土地上,只要政治上不幸了,你便无路可走。
很后悔,没为他写一个字——张超英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读后
张超英身为台湾新闻处的公务员,在工作中却能淡化意识形态,摆脱官方样式,他的口述回忆录并不求把“事说得周周正正”,而是随意自在,并充满了独立的判断。
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?——读李长声
李长声是“日本通”,书也写得好,所写涉猎极广,“像个万花筒,拿起轻轻一摇,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”,像他笔下的日本艺妓就非常出色。
先天禀赋,后天学养——读唐德刚
我从唐德刚“口述历史”的写作中学到了要深入研究人与人、人与环境和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,他个人化的语言“充满了文学的魅力,也充满了真知灼见”,张扬而非肆意妄为,“最懂人心与人情”。
史学研究还有一部分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,那就是在史学之中,还有文学。(唐德刚)
衔石成痴绝,沧波万里愁——《双照楼诗词稿》有感
父亲纠正我说历史书里的汉奸汪精卫并不完全属实,对他的看法可以用“漂亮,才情,人品”来概括,汪诗是哀国之音,也蕴含着一个“精卫情结”(引叶嘉莹),不管现实中是否做得到,“内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”。
将军空老玉门关,读书人一声长叹——白先勇《父亲与民国》读后
白先勇是一个出色的诠释者,他的图注“把每一行字,都视为步步危棋,下笔克制谨慎”,白氏作品贯穿着“伤逝之情”,体现了浓重的历史关怀,同时又恪守诚实。
谁道人生无再少,门前流水尚能西——说白先勇
白先勇“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,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”,“他的作品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,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”,作者简要回忆了自己和白老的交往,印象深刻的是吃桂林米粉和他“通人情、好人缘”的“君子”品质。
水深水浅,云去云来——说林青霞
作者与林青霞私交甚好,也互相欣赏,在我眼中,林青霞“不说是非,但心里是有是非的”,而林又十分喜爱我文字中的“热情、正义感和勇气”,又谈到艺人其实是“胆小”,表面上风光,但内心往往脆弱和有卑微感,相识后我走入到林的孤独世界中,也看到她在拿起笔写作之后发生的变化,她的文字“真实而细腻”,“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”,让人感动。
泪往下滴,血朝上涌——胡发云《如焉》序
由于亲人同样死于绝症,病痛与死亡成了我和胡发云相识伊始常聊的话题,他给亡妻的悼文“深深震动了我”,我认为他是父亲所说的“懂得女人的男人”,文中胡发云感叹道:“五十一年的生命。三十年的相识。二十六年的夫妻。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,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。这种美,只有种花的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……哪怕凋萎,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。”至亲离世之后,我和他都是“半生半死人”,但都还“有话要说”,在“并不怎么好”的现实面前,唯有写作才能“激活生命”,《如焉》和《伶人往事》双双被禁,我们彼此互相鼓励。
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,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。
在被无视和被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,人们真实地活着比获得成功更为重要。
弦管谁家奏太平——野夫《尘世·挽歌》序
野夫本来在公安局工作,八九年后愤然辞职,开始逃亡,出狱后给别人编书无数,只有这本属于自己,“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”,“我读到的是他的心,看到的是他的泪”,在我看来,现在已经没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唤醒这个“已然入睡”的民族。
他记下了那个夜晚——阅读李晓斌
摄影家李晓斌用胶卷和相机快门记录下八九年的那个夜晚,引出我对纪实摄影的思考,并感叹亚里士多德所言“诗人比历史学家更真实”。
艾未未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
简要介绍了艾未未的艺术风格,代表性作品,梳理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脉络(八十年代末的文化批判,九十年代初的波普特征,九十年代中期强调使用自身的肢体语言表达生存的艰难,和后来以艾未未为代表的社会批判)。
一草一木皆春秋——说张思之
一直劝大律师张思之写回忆录,终于在孙国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口述史,张大律师“是一个极富真知灼见的人”,他和我都认为“八九学生领袖是中国历届学运里素质最差的”,并佩服王军涛的光明磊落,他“为人老辣,下笔也老辣”。
女囚与性
《刘氏女》到《钱氏女》,里面的人物和犯罪事件都有原型,虚构的部分极少,也融入了自己很多感受和感情;和政治犯不同,刑事犯在监狱中“特别渴望情感、渴望温情”,“除了每天劳动,生命欲望是她们的精神中心”;多次引用李银河,来论述自己对性快乐、性的意义和对同性恋的包容等问题;最后感慨命运无常,刑满出狱的周氏女发现生活早已变样,让她痛苦不堪,“生命是一个故事,还是一个事故?”
倘若在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,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实;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。(李银河)
年轻的时候,总以为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。经历了许多之后才明白:其实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有无数个解,而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。
叶有败落,花已凋零——关于写作及父辈的话题
通过回溯父辈的民盟和自己写作的经历,讲述中共统战对民主人士的打压。
陈姑娘,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
追忆已故歌手陈琳,偶然相识,被她身上的热情、温柔与脆弱打动。“人生的痛苦,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,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。”
问病记
记述了一次赴台探望身患肝病好友的经历,签证的拖延,浩子特意调换病房脱下病服热情接待,和他女儿在换肝前动情的信,让人再一次领悟活着的意义。
悲回风——追忆我的老师
简慧老师是我在戏曲学院的老师,后来在戏曲研究院工作又成了同事,由于“出身”别人都躲着我的时候,“她接纳了我”,工作上她兢兢业业,不问得失,“是用近乎伟大的精神做近乎无用的工作”,研究戏曲则从研究艺人出发,是一个十足的内行,但在“商品大潮”袭来时却不被重视。其实简老师出身富贵,年轻时决定“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革命”,虽然“这个时代对不住她”(因为晚一天参加革命,最后连“离休”待遇都没有拿到),但她“心甘情愿且始终不悔”。“我觉得简老师的一生曲折又平淡,所有的转折点都充满意味,时代的意味,很深刻,很沉重”。
我们或是主动、或是被动地奔走在匆忙的现实中,也许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动得稀里哗啦,但内心的情感却如尘埃一样吹到远处,人伦、亲情、故土、亡灵等许多值得珍视和珍藏的,都变得无足轻重,无关紧要。
我们有“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”吗——香港《明报月刊》与浸会大学文学院关于“价值中立的文化空间”讨论的发言
提出“真实是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”,而不是诸多价值之一,反对“作家艺术家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”,对当代作家有意回避作品中的政治意识、思想意识,把感官享受和世俗性事物作为唯一目标感到遗憾,因为“越是世俗的生活,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”,不然很难称得上人文关怀。中国社会一直“不怎么容得中间立场”,官方的指责和对作者的批判已是常态,几十年来“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”。
还原文人、艺人的生命状态——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座谈温家宝总理在文代会与作代会讲话的书面发言
文人就是“舞文弄墨者”,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放浪不羁,身上也有形形色色的“颓唐行为”,但在内里又“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”,我爱说这些“民国旧事”,正因为这些“耐人寻味”的人生在四九年后“大多为红色政权所不容”(彭真委员长是个例外),现在的文学家、艺术家都被管得“左右不是,上下不能”。
我看到了许多微笑——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颁奖会上的答谢辞
文学是“人学”,是“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”,与“官学”无涉,与“官场”无干。
把心叫醒,将魂找回——致谢(美国)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
我深知:生命的延续不等于人生之收获,故每日都有光阴从指尖前滑落的焦灼。